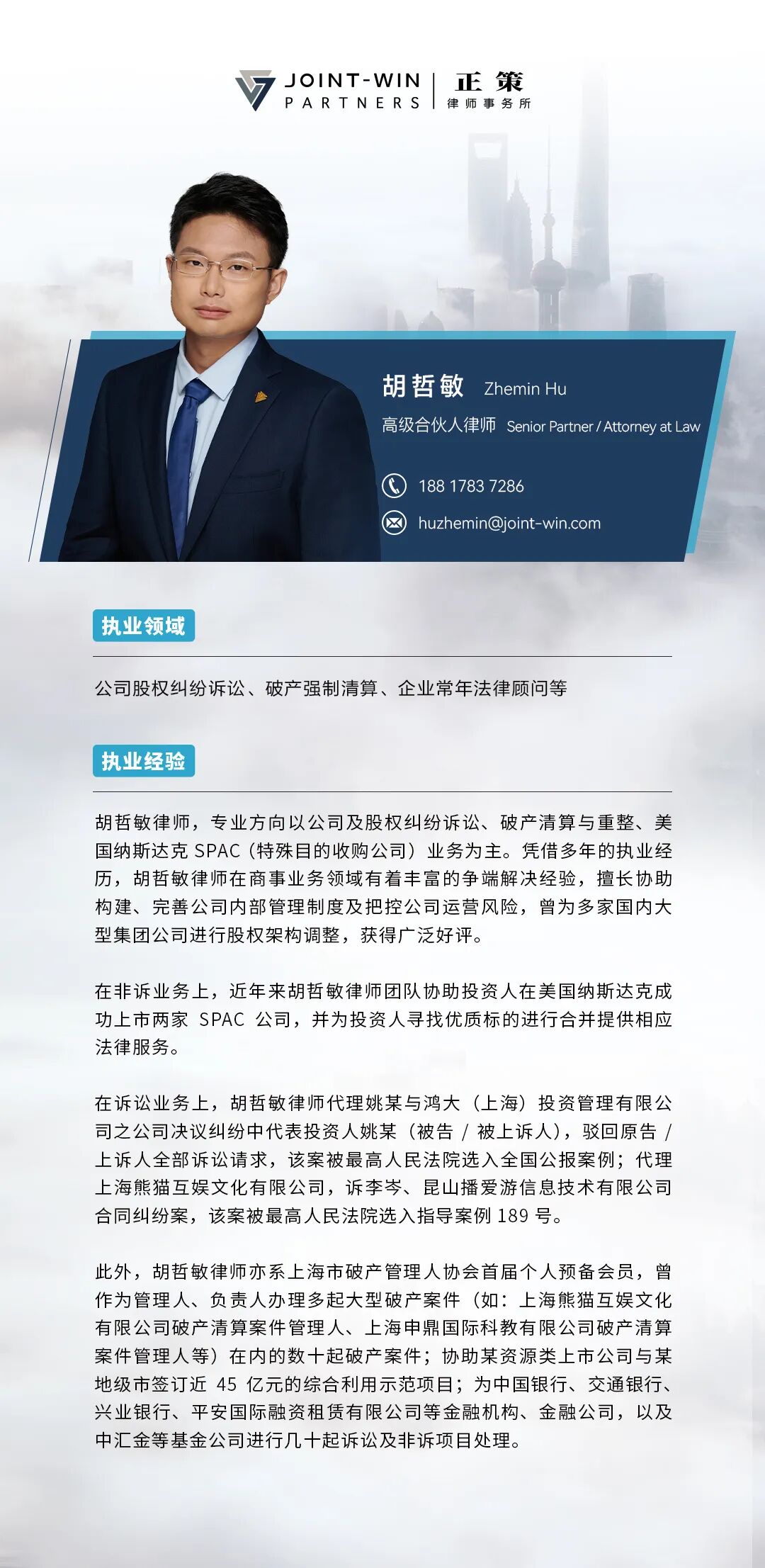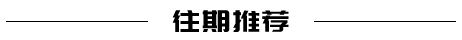正策新闻
正策关注|《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溯及力争议破解:恶意股权转让债权救济的实务路径——以宝姿公司破产追收案为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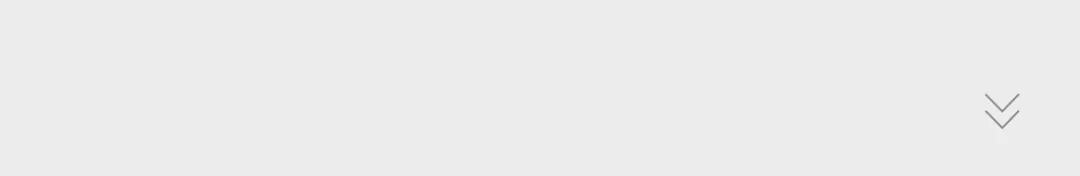

问题缘起:《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溯及力争议的实务困局
2024年7月《新公司法》施行,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明确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责任:“受让人承担出资义务,转让人承担补充责任”,终结了旧法下“同案不同判”乱象,为债权人追索前手股东提供直接依据。但同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规定该条款仅适用于2024年7月后股权转让,此前纠纷需“依原公司法精神处理”,使旧法时期纠纷重回法律适用模糊地带。
《批复》出台后,大量依托新法起诉的案件陷入困境,据破产管理人群体反馈,相关案件撤诉率升至41%,85%代理律师需重构法律依据。上海宝姿化妆品有限公司(下称“宝姿公司”)破产追收案正是典型样本——一审以新法为论证思路,《批复》出台后二审策略紧急调整,最终通过旧法法理与证据链实现债权清偿,其经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案例透视:从形式裁判到实质正义的突破路径
(一)案件基本僵局:股权腾挪下的债权清偿困境
宝姿公司2023年陷入经营困境并进入破产清算,工商登记唯一股东为年近八旬的张某(前股东龚某父亲),认缴出资3900万元但无实际偿债能力。经确认核心债权约92万元,公司账面仅余532.6元,债权人面临零清偿风险。追溯股权变动,2017年7月纪某、昌华公司分别以1元对价将60%、40%股权转给龚某;同年11月龚某以0元对价将全部股权转给张某,转让过程无合理对价,且发生在债务集中形成期。
(二)一审裁判局限:“债务确认时间”的形式化认定
一审中,管理人主张张某履行出资义务,龚某等前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支持张某出资诉请,但以“无证据证明转让时存在司法确认债务”为由,驳回前股东连带责任诉求。该形式化裁判忽视债务真实形成时间与司法确认的时间差,机械的以司法确认作为债权形成的时间节点,恶意股东恰利用此实施股权腾挪,导致“胜诉却无财产执行”,违背破产法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宗旨。
(三)二审策略重构:“实质恶意”的证据链构建与法理辩驳
1. 核心策略的调整:
《批复》出台后,代理团队放弃“新法溯及适用”思路,转向以“恶意逃债”为核心的实质论证,龚某、纪某等人2017年的股权转让行为,本质上是“为逃避既有债务而进行的恶意转让”,上诉请求与论证核心,全部紧紧围绕这一实质性问题展开针对辩论,构建四维证据体系:
债务形成在先:我们强调,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于其自然形成之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核心债权人陈某的工资债权与民间借贷债权,其事实形成于2017年4月至10月,均明确早于同年11月28日的关键股权转让时点。这证明了转让发生时,公司对外负债是一个既成事实。
偿债能力丧失:为了突破僵局,我们调取重点呈递了另案的生效判决与执行裁定。这些文书显示,在股权转让前,宝姿公司已因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等多起纠纷被多家债权人起诉并申请强制执行,且法院均因“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此外,鉴于破产企业并未交付财务资料,我们还向税务机关调取了2016~2018年期间的资产负债表等财务备案资料,从资料中直观的向法院反应了宝姿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这足以证明,在股权转让时,宝姿公司早已具备《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而非正常的经营实体。
转让对价异常:3900万元认缴资本通过“1元+0元”对价转让,明显背离商业常理,指向逃债目的。
受让方履约能力欠缺:我们突出强调了受让人现任股东的特殊身份与状况。他不仅是转让人龚某的父亲,受让股权时已近80岁高龄,且在其本人陈述中明确表示“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选择一个无出资意愿、无经营能力、无财产基础的老人作为公司唯一股东,其逃避未来出资义务的意图昭然若揭。我们向法庭清晰地呈现整个股权转让过程均在龚某、纪某、昌华公司及其关联亲属(现任股东)之间完成,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脱离正常市场交易的内部闭环。这种关联性交易,极大地强化了其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推定。
2. 二审庭审的攻防抗辩: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纪某提出三类典型抗辩,代理团队逐一针对性驳斥:
一是300万元转账性质抗辩:纪某主张2015年向公司的300万元转账为出资款。代理团队指出,股东出资属要式法律行为,该款项未备注“出资款”,亦未履行股东会确认、章程记载、工商公示等法定程序,属股东借款或资金往来,不能以内部资金关系推翻公司对外认缴未实缴的公示状态。
二是出资期限利益抗辩:纪某以“转让时出资期限未届满”主张享有期限利益。代理团队回应,期限利益是诚信股东的权利而非逃债“护身符”,恶意逃避债务的转让行为构成权利滥用,违背《公司法》第二十条禁止滥用股东权利原则,符合《批复》要求的“原公司法精神”。
三是核心债权真实性抗辩:纪某质疑核心债权存在串通可能。代理团队明确,该债权经破产审查、债权人会议核查及法院裁定确认,具有司法公信力,对方无证据推翻生效法律文书,主观猜测不能成立。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作出二审判决,全面采纳了代理团队的论证意见,在裁判思路上实现了重要突破,作出了具有标杆意义的裁判结论:
摒弃形式化标准:不以“债务司法确认时间”为唯一依据,综合债务形成时间、公司偿债能力、转让对价合理性等作实质判断,契合商事审判“穿透式审查”理念;
精准认定恶意:判决书明确指出,二审补充证据已然证明股权转让前已经符合资不抵债的情况。宝姿公司已存在大量到期债务且经强制执行仍无力清偿的情况下,纪某等人以零对价将股权转让给无出资能力和经营能力的年迈亲属,“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惯例”,足以认定其具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
明确责任承担:改判前股东龚某、纪某、昌华公司在原告主张的债权范围内对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判决生效后,前股东纪某因具备偿债能力,于30日内将原告主张款项全额支付至管理人账户,债权人债权100%清偿,实现“裁判到执行”闭环。该案成为《批复》出台后上海法院实质审查恶意股权转让的典型案例。

证据组织:聚焦“恶意逃债”的四维事实闭环
处理2024年7月前股权转让纠纷,需构建“恶意逃债”四维证据链:一是债务形成证据(合同、凭证等)证明债务早于转让;二是偿债能力证据(涉诉、执行记录)佐证公司无清偿力;三是转让异常证据(对价凭证)揭示无偿或低价转让;四是关联关系证据(亲属、关联企业信息)强化恶意推定,证据按“时间+逻辑”编排便于法院审查。
法律适用:以新法精神衔接旧法原则
《批复》未关闭救济通道,需以新法精神衔接旧法原则。《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禁止恶意逃债”精神,可指引《公司法》第二十条的适用:恶意股权转让中,股东主观有逃债故意,客观导致债权人损失,因果关系明确,构成滥用股东有限责任,据此可在旧法框架下追责。
破产程序:从形式清收到实质救济的转型
破产程序应强化实质清收,管理人需建立“股权变动全链条追溯”机制:审查近五年股权变更,重点核查低价/无偿转让,结合债务与偿债能力判断恶意,及时诉讼追收。法院应加强指导,注重实质审查,避免财产流失。通过程序衔接,将恶意股东纳入责任主体,提升清偿比例与破产程序公信力。

宝姿公司案表明,旧法时期恶意股权转让纠纷可通过回归法律原则、构建证据链实现救济。该案彰显实质正义取向,为同类案件提供范本。未来需完善“恶意逃债”认定标准,提升管理人追收能力,通过法理与证据结合破解难题,筑牢市场经济司法保障防线。
文章内容仅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本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