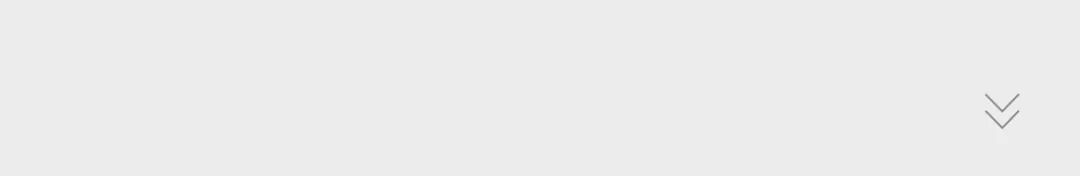《情况通报》内容中提到“少林寺住持……”,原因在于住持与方丈在一些情况中可以指代同一人,但实际上两者含义并不相同,住持为职务名称,而方丈则是佛学精神层面的尊称。2024年中国佛教协会审议并通过新修订的《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中定义住持为"汉传佛教寺院主要教职","对外代表常住,对内统理大众",并对担任住持做出年龄等条件要求。其中第四条明确,住持的产生必须贯彻民主协商、选贤任能的原则,由该寺前任住持或管理组织提出人选,再由寺院所在地佛教协会按照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条件对住持人选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提交该寺院两序大众民主评议;需经两序大众民主评议获半数以上赞成,再由寺院管理组织书面报告所在地佛教协会;协会审核同意之后,再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也因此,寺庙住持的选任流程上存在严格的审核需求,但对于实质性审核内容等,却并未予以明确。“方丈”一词是由于古代僧房都是以边长一丈的四方形作为居住的空间,所以称为方丈室或丈室。《维摩诘经》中记载,维摩诘居士在"一丈之室"容纳无数听众演说佛法,赋予“方丈”深层宗教意义。目前实践中方丈则是精神权威的象征,不在现行法律范围内予以规制。另外,“方丈”一词不仅限于佛教领域,道教领域也以“方丈”谓领袖人物。一般认为,宗教财产是一种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因宗教信徒捐助或国家扶持而积聚形成的特殊财产,其在物质形态上包括以下四种类型:第一,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员占有或使用的主体建筑及附属设施;第二,宗教建筑及附属设施占用的土地、山林、草原、田地等;第三,宗教经籍文献、法物以及宗教无形财产;第四,其他宗教财产及获取的合法收益。(参考《宗教财产归属与宗教法人资格问题的法律思考》,冯玉军)。因此,少林寺等有关寺庙的财产主要可以分为:3)具有宗教性质的文献以及无形财产(如知识产权);4)寺庙其他财产以及取得的合法收益,如信众捐赠、租金、宗教活动收入等。《宗教事务条例》以第七章专章对宗教财产予以规制,其中第四十九条载明,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对依法占有的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的财产,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对其他合法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但对于以上四大类财产在实践中究竟如何管理、如何保证财产独立以及如何使用,在实践中仍然没有定论。《民法典》虽明确了寺庙等宗教活动场所可以取得捐助法人资格,但对于宗教财产的归属并未在其中规制,导致实践中产生了众多乱象。2013年3月,多位政协委员曾就佛寺景点乱象提出意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曾提及,一些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搞宗教活动,以教牟利,借教敛财,把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上市,企业或个人对寺庙进行投资经营或承包经营,冒充佛教教职人员进行违法宗教活动、非法牟利。实践中,仍不乏将寺庙收益包装为金融产品或予以上市,或投资或承包予以敛财。而寺庙也往往与景点或地址接近、或互相包容,联名门票、香火、周边产品的费用收入如何认定,都存在争议,也因此萌生牟利。放在释永信案件中,这个具体问题就成为了资金来源有几种?如何认定非法性?以及与少林寺有关的公司收益是否属“寺庙财产”?(一)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
根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宗教活动场所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犯罪主体的批复》公经〔2004〕643号载明:“根据《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5号令)等有关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属于刑法第271条和第272条所规定的“其他单位”的范围。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属于公共财产或信教公民共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和非法处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或挪用宗教活动场所公共财产的,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批复将“宗教活动场所”认定属于刑法第271条和第272条所规定的“其他单位”的范畴。但对于“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员”身份并未予以具体化。根据《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全国性宗教团体应当在业务范围内制定本宗教的宗教活动场所规章制度,对场所管理组织成员监督及其任期、宗教教职人员、主要教职、宗教活动、财务和资产管理等作出具体规定。若在宗教团体中,存在有关管理组织成员的任命,都有可能被认定为“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员”。同样,“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缺乏定义。以(2019)闽07刑终183号案件为例,法院将寺内建立的养老院所销售床位而收取的款项与对外以寺院名义进行的借款一并认定为犯罪所得,但是对于辩护人二审中提出的对罪犯任住持期间的财务和资产进行审计要求予以驳回,最终认定周某某构成职务侵占罪。(二)最高检答复:佛教协会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主体
《关于佛教协会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问题的答复》2003年1月13日([2003]高检研发第2号)载明:“……佛教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其工作人员除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外,既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根据刑法的规定,对非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不能按受贿罪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经检索,从裁判文书网系统上关于寺庙住持利用职务之便可能犯有的刑事犯罪中,确实未见有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但职务侵占罪却不少见。基于寺庙的宗教属性,天然可以具有招揽信徒、对外盈利的优势,而寺庙住持的身份加持,往往使得罪犯极具被信任度,在此基础上,由于许多小寺庙并不具有合格出纳、资产管理混乱、毫无内部管理的情况,往往采取传统的“刷脸”借贷模式——住持个人以寺院名义对外借款,导致住持与宗教活动场所产生混同,极易滋生犯罪。我们认为,宗教治理法治化需要先解决宗教财产权属问题。梁慧星教授曾就《物权法(草案)》提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私人财产、国家机关财产、事业单位的财产、社会团体的财产在《物权法(草案)》当中都有具体的规定,唯独宗教财产没有规定”。宗教财产的权属解决从目前环境看,既符合我国“反洗钱”策略,符合税收政策,同时也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必然,否则就会造成宗教问题小则忽视,大则涉及刑事的局面,在国家治理角度缺乏缓冲,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可能不利于宗教保护、不利于民族稳定。宗教信仰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稳定效果,理应予以保护,财产权属明晰可以有效区分财产属性、防范出现非法事件,另一角度来说,有效的财产权属明晰也是对合法财产予以保护,防止出现涉刑之后财产损失难以追回的场景。但我们也认为,从目前立法体系来看,宗教场所不同于公司、企业,具有其特殊性,也可以设立专条或专款,对于宗教财产予以分类,从而引导不同部门法律的适用与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