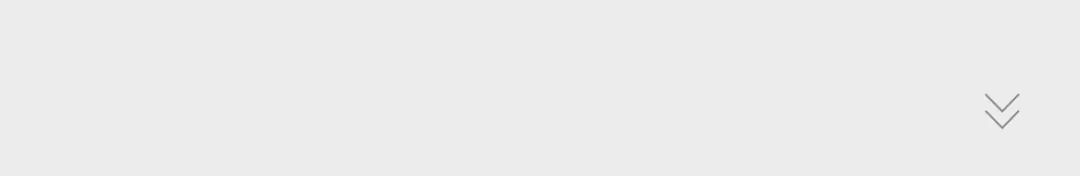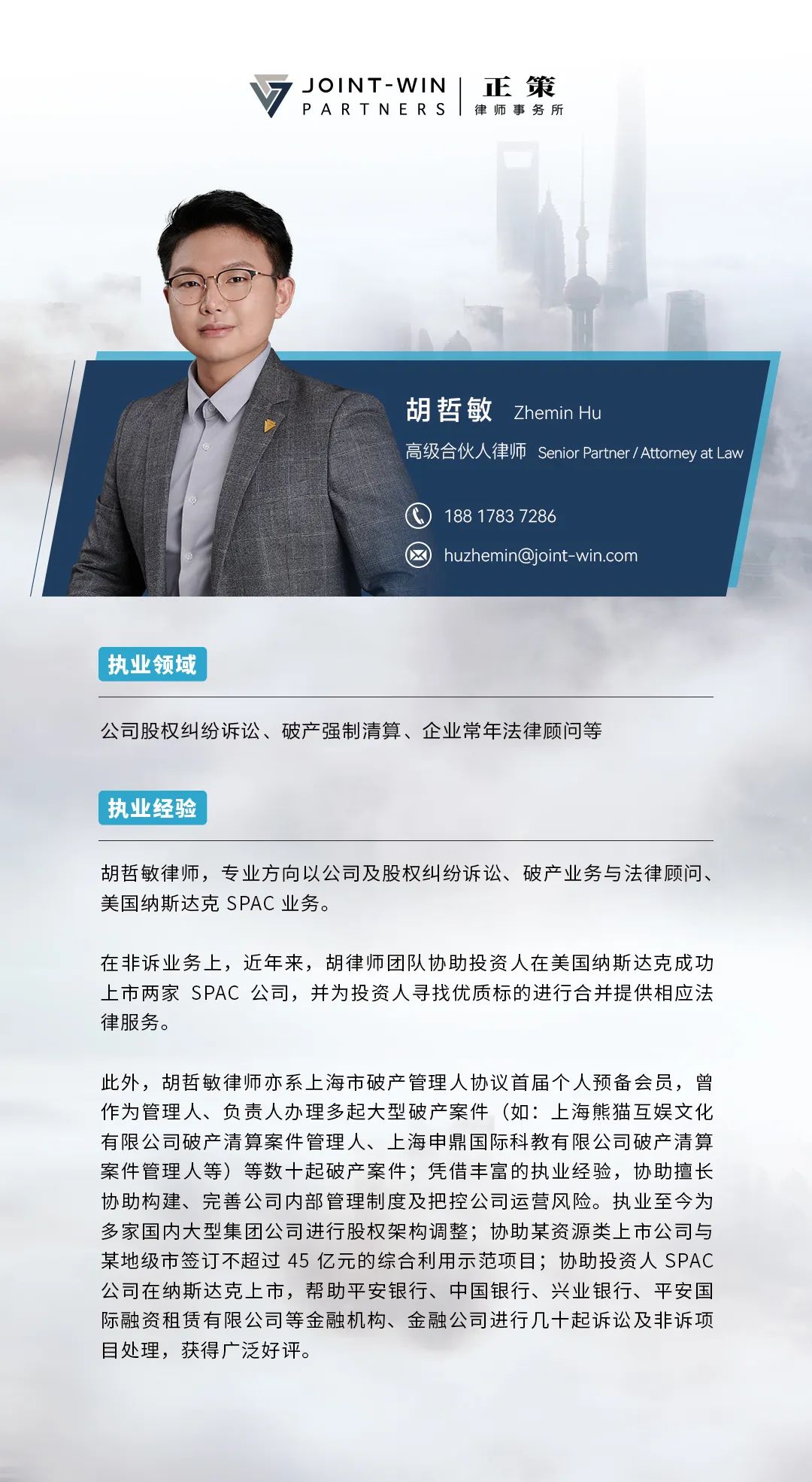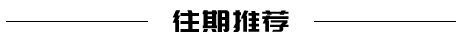正策新闻
正策关注|存在股权代持情形时,破产程序中追缴股东出资的责任主体认定规则
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 《企业破产法》第35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行使追收未缴出资请求权时,显名股东(即登记股东)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构成首要责任主体。然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及禁止权利滥用之考量,在特定情形下可以穿透代持关系将隐名股东纳入责任主体范畴。本文以《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规范体系为基准,结合司法裁判要旨,对此进行类型化分析。

责任认定之规范基础与价值取向
(一)商事外观主义之优先性
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及《民法典》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商事登记事项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显名股东作为登记公示之责任主体,须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资本充实责任。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在(2023)沪7101民初294号判决中明确:"工商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代持协议仅具内部约束性,显名股东不得以股权代持对抗管理人基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要求其履行的法定出资义务。"此裁判要旨彰显了商法领域外观主义原则的优先适用性。
(二)代持法律关系内部相对性之效力边界
破产程序具有集体清偿属性,《企业破产法》第一条开宗明义确立"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之立法目的,强调了破产法项下程序效率价值对个别股东权益的优先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至二十七条确立股权代持法律关系之内部相对性规则,隐名股东仅得依据《民法典》合同编向显名股东主张权益,该等请求权基础不得对抗破产管理人基于法定职权行使的追收权。在(2023)沪7101民初2173号案件中,法院指出:"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间《股权代持协议书》仅具债法效力,不能产生对抗公司外部第三人之物权变动效果。"此裁判逻辑与《九民纪要》第二十八条关于实际出资人显名化要件之规定形成体系化呼应。
然而,在破产程序中,尽管管理人向股东提起追收未缴出资诉讼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追收的出资款清偿外部债权,但其在身份上代表的是债务人公司,并非外部第三人。公司请求隐名股东足额缴纳出资属于公司内部治理问题,部分法院认为法院应当结合形式性与实质性审查,着重审查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来认定股东资格及附带的出资义务。在(2019)京民终1515号案件中,法院经实质审查,将显名股东、隐名股东、其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协议作为判决隐名股东承担出资责任的依据。
责任主体穿透认定之裁判规则
(一)显名股东责任之法定性
1.形式审查标准
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履行职责,接管债务人财产。管理人追收出资时仅需对股东资格进行形式审查,即“登记推定主义”。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6号判决明确:"工商登记信息系判断股东资格的初步证据,显名股东未实缴出资即应承担补足责任。"显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间的内部约定不影响管理人追收权之行使。
2.抗辩事由的严格限制
显名股东以代持协议抗辩的,法院通常援引《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予以驳回。如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74民终987号判决指出:"股东出资义务系法定义务,不因代持合意而免除。"
(二)隐名股东责任穿透之实质要件
破产程序中,隐名股东承担出资责任的审查要点在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及《九民纪要》第二十八条,以公司名义请求确认隐名股东“显名化”,其核心是:“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实际出资人显名”。具体到案件中,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三要素分析法"认定隐名股东责任:
(1)代持合意之客观证据(书面协议、往来函件)
(2)实际控制公司经营之持续性(财务审批记录、重大决策文件)
(3)资本形成之真实来源(出资账户与隐名股东财产混同)
特殊情况,隐名股东对显名股东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存在上文隐名股东穿透的情况下,部分法院是以连带责任认定,如(2024)湘1121 民初 340号案件在进行上述实质审查后判决隐名股东对显名股东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
(一)一般规则 管理人直接起诉显名股东,显名股东补缴出资后,可依据代持协议向隐名股东追偿。
(二)例外突破 当管理人初步掌握上述股权代持线索后,将隐名股东一并作为被告,要求其对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将更有利于提高债权的清偿可能性。
(三)其他方案 当隐名股东实际控制公司、存在欺诈或恶意行为时,管理人可另行以隐名股东的恶意行为或实控人身份提起其他诉讼追究其责任。
文章内容仅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本所立场